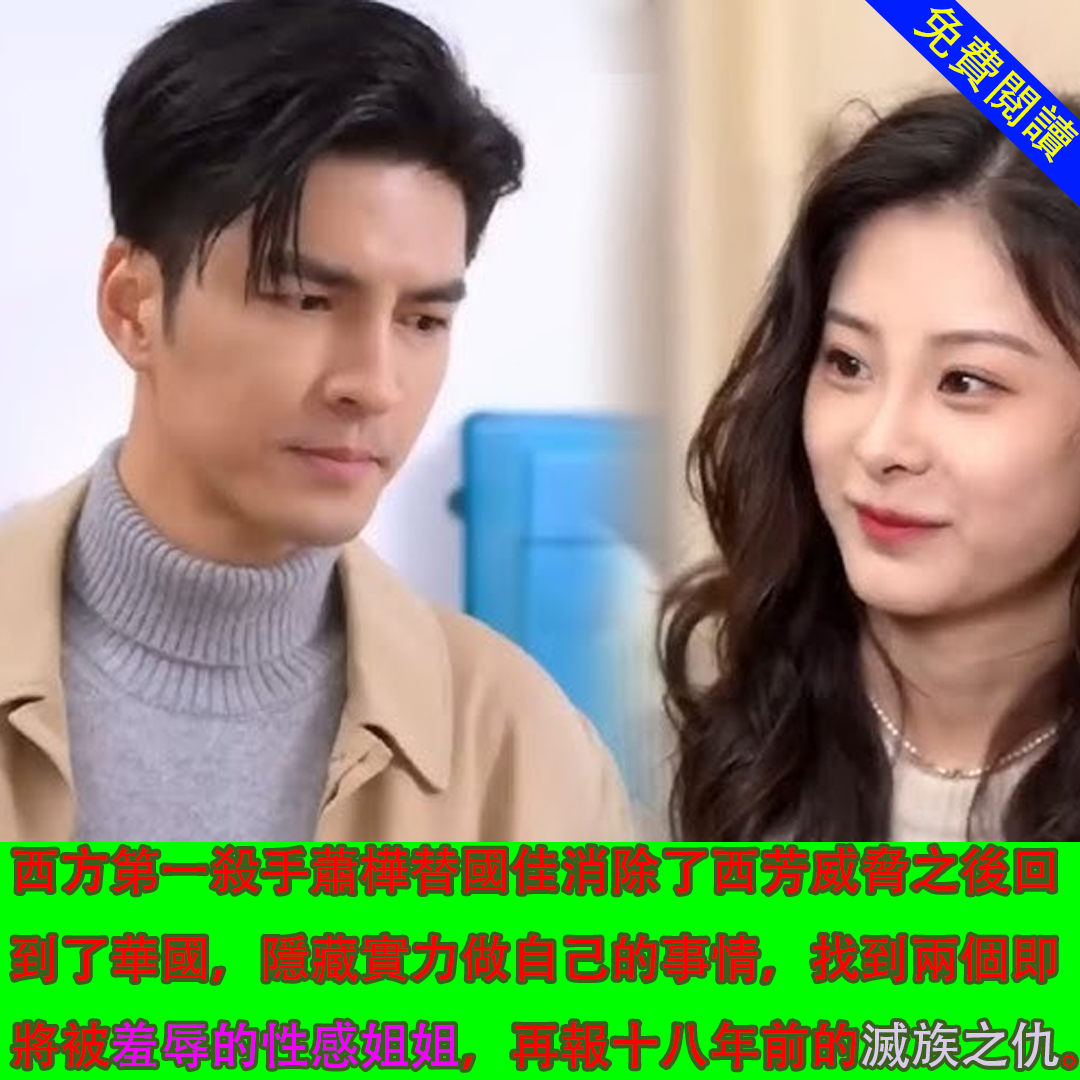半夏把匣子打開,從匣子裡拿出厚厚一摞方子,蘇棠看方子很快,就跟看書一樣,一目十行,也看了足足一刻多鐘。
一張不落的掃完,蘇棠眼睛都看酸脹了,将最後一張診脈方放下,拓跋擎的聲音就傳了來,略帶一絲緊張,“隻看這些方子,護國公主能醫治家母嗎?
”
蘇棠道,“看九位太醫的診斷和過往服用的方子,令堂得的應該是心悸之症,服用的這些藥方都挺對症,令堂卻一病幾年,久治不愈......”
“應該不止是心悸這麼簡單,可惜令堂不在,不然我能親自給她把脈。
”
雖然九位太醫都寫了脈象,但方子差别在表述上,把出來的脈象都是一樣的。
蘇棠直言道,“沒法把脈,我隻能憑經驗醫治了,令堂要麼是中毒了,毒性輕微,太醫把不出來,要麼令堂得的是心病,令堂心底有難以釋懷之事,日日折磨她,終日寝食難安,心病不除,服用再多的藥也隻能緩解一時,難以根治。
”
拓跋擎身子一僵,他身後站着的護衛肅然起敬。
難怪甯朝護國公主醫術超絕都傳到他們東厥去了,隻看把脈和服用的藥方子都能猜到她們皇妃娘娘有心病,醫術确實非同凡響。
拓跋擎點頭,“家母有沒有被人下毒,我不知道,但家母确實有難以釋懷之事,經常吃不下,做噩夢。
”
蘇棠道,“那令堂的心悸十有八九是心病了,看脈象,令堂除了心悸之外,其她都還好,沒有性命之憂,眼下我懷着身孕,沒法前去東厥,我調制些養生丸你帶回去給令堂服用,盡量開解令堂,消她心病,若心事解了,心悸之症還沒有好轉,屆時我腹中胎兒已經生下,我親自去東厥醫治令堂。
”
蘇棠好說話的不行,都說伸手不打笑臉人,人家千裡求醫,這份看重就值得她好好相待了,再者拓跋擎求她治母,朝廷也在求拓跋擎,希望能從東厥多弄些糧草。
拓跋擎心下苦笑,想消他母親的心病談何容易......
至于心病是什麼,拓跋擎沒說,蘇棠也沒問,她遠在甯朝幫不上忙,做大夫的隻能醫身,醫不了心。
而且蘇棠也沒機會問,外面丫鬟進來道,“世子妃,信安郡王妃來了。
”
馮媛這時候來肯定是帶她姨母來治病的,蘇棠得招呼她,拓跋擎就起身告辭,謝柏庭送他出府。
蘇棠随他們一起出了正堂,目送他們出靜墨軒,收回眸光時,正好巧兒回來,她身上沾了不少泥巴,紅菱問道,“你這是怎麼了?
”
巧兒癟着小嘴,眼淚滾下來,“不小心摔了一跤,隻能明兒再出去接着找人了......”
好不容易世子妃安排她個差事,偏她沒用,在街上找了幾天,連個人影也沒瞧見。
紅菱就道,“沒摔壞啊,京都這麼大,這個人确實不容易,慢慢找,别着急。
”
巧兒點頭如小雞啄米,揉着摔疼的胳膊肘回去換裙裳。
這邊巧兒回下人房,那邊馮媛領着李家大太太走進來,身後還跟着兩丫鬟。
瞧見蘇棠,馮媛笑容滿面,蘇棠迎上去道,“可算是來了。
”